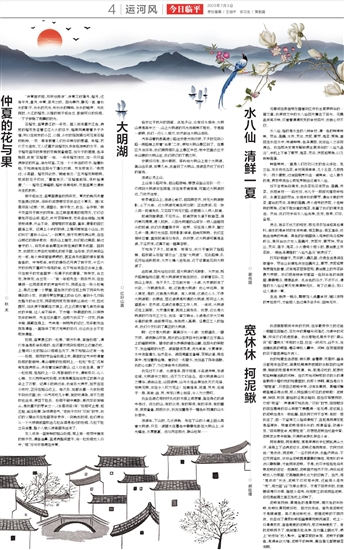○ 秋禾
“仲夏苦夜短,开轩纳微凉”,仲夏又称蒲月、榴月,还有午月、星月、中夏、恶月之称。阳光暴烈,静无一言,看长长的影子、长长的天光,听长长的蝉鸣、长长的蛙声。与此同时,火红的榴花、淡雅的栀子和白兰、酸甜可口的杨梅,一下子惊艳了微醺的时光。
石榴花,盛夏最红的一朵花。国人向来喜欢红色,满枝的榴花象征着红红火火的日子,榴果则寓意着多子多福,所以在城市的小区、公园、乡村的庭院随处可见有石榴树栽种,一花一果承载着人们朴实美好的愿望。咏榴,历代不乏佳句,文人还喜欢将榴花比作年轻貌美的女子。由于榴花盛开时微卷的花瓣层叠错落,如女子的裙裾,色泽艳丽,故有“石榴裙”一说。一朵朵榴花绽放,如一只只盛满琼浆的杯盏,油光可鉴;又如一个个快活的孩子,摇着铃铛,不知疲倦地在阳光下嬉戏打闹。苏东坡有云:“微雨过,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燃。”韩愈有云:“五月榴花照眼明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”曹植有云:“石榴植前庭,绿叶摇缥青。”……榴花红得耀眼,榴叶绿得纯粹,尽显盛夏之清新与生机勃勃。
栀子和白兰,盛夏里最香的两朵花。夏夜的晚风夹着花香拂过肌肤,深呼吸间想要紧紧抓住这个夏天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卮,酒器也。栀子象之,故名。俗作栀。”栀子花盛开于南方的雨季,在江南湿漉漉的梅雨天,它们恣意地开在山间、路边,叶片苍翠鲜绿,花朵洁白凝脂,如绸缎般润滑,纤尘不染。湿嗒嗒的花香里,童年、青春的回忆翻涌上来。记得上小学的时候,上塘河南有座小山丘,我们叫它“星桥小山头”,一到夏天,栀子花便开满山坡,住在山脚边的同学邀我一起去山上摘花,我们越过篱笆,躲过看守的人,将花朵偷偷藏在斜挎在肩的黄书包里。回到家,我把花儿养在吃完腐乳的瓶子里,给母亲、奶奶房间各放一瓶,每个房间都香喷喷的,甚至连书包里的课本都是香香的。中考那年,学校的操场边开满了栀子花,十五六岁的我既不懂何为纯纯的爱,也不知后来自己会爱上谁,只在栀子的花香里梦一场属于我的青春。“珠珠花,白兰花,珠珠花,白兰花……”有一年和先生一起去苏州,在古镇被一位阿婆柔软的声音所吸引,阿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,身边立着一个箩筐,蓝色布衣的纽扣上别了两朵玲珑精致的小花。我揭开蒙在箩筐上的白毛巾,看到十几对码放整齐的白兰花,阿婆把两枝花用细铁丝连成一对,扭成圆环,如此便于佩戴在衣襟上,边上还摆放着几串花朵编成的手链,让人爱不释手。下方铺一块潮湿的布,以保持花朵的鲜妍。先生见我喜欢,当即为我买下一对花、两串手链,佩戴在身上。气味是一种特殊的记忆,花朵散发出阵阵清香,一直陪伴了那次完美的旅行,也让我念念不忘那抹清香。
杨梅,盛夏最红的一粒果。“南方珍果,首推杨梅”,清代李渔是极爱杨梅的,他还喜欢爬到杨梅树上边摘边吃。上塘河以北的超山以梅闻名天下,殊不知超山还有一绝——杨梅。梅雨时节恰逢杨梅上市,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杨梅的酸甜味,漫山遍野的杨梅树上,一粒粒“紫红”沉甸甸地挂满枝头,点缀着如黛的青山,让人口舌生津。摘下一粒杨梅,轻轻咬上一口,那酸甜的汁水,清新爽口,沁人心脾。女儿特别爱吃杨梅,我常常嗔怪她将紫红的果汁沾染上了衣服。记得小时候过年,我爱去大姨家,她家住在小林村,正好在超山边上。每次去,她都会塞一大包杨梅干到我怀里,我一口气可吃几十颗,有时吃得急,来不及把核吐出来,便吞下肚去。杨梅干甜中寓酸,果肉紧致有嚼头,是我喜欢的零食之一。《本草纲目》写:“杨梅可止渴、和五脏、能涤肠胃、除烦愦恶气。”老底子农村“双抢”时节,我们的父辈白天在地里艰辛劳作,一到晚饭时间,他们便会从一个大玻璃瓶里取出几粒白酒浸泡过的杨梅,几粒下肚立马消暑,整个人就从疲惫里走出来了。
友人送来一篮新鲜的超山杨梅,案上有一枝雨中摘来的栀子花,清香溢鼻,盈漾满整间屋子,将一粒杨梅放入口中,“梅”好与你相遇在仲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