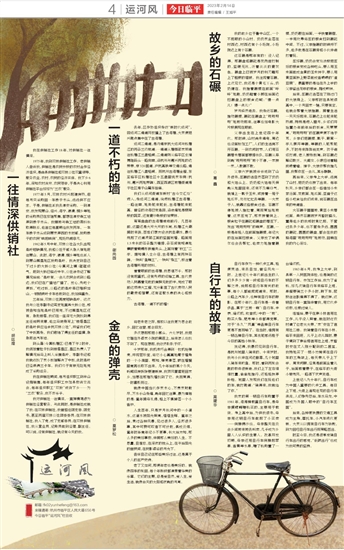○ 葛 鑫
我的故乡位于鲁中山区,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。奶奶家坐落在村西边,村西边有个小场院,小场院边上有个石碾。
这石碾是哪年有的?没人记得。那碾盘和碾砣是花岗岩打制的,坚硬无比,泛着淡淡的青灰色。碾盘上已被岁月的利刃雕琢上了粗粝的褶皱。我注视着石碾,上次见它,我还是个黄毛丫头,奶奶健在。我推着碾棍在前面“呼呼”地跑,奶奶踮着小脚在后面边扫碾盘上的粮食边喊:“慢一点儿!慢一点儿!”
岁月倏然逝去。我走近石碾,推动碾棍,碾砣在碾盘上“吱吱呀呀”地转动起来,往事也如电影大片般展现在眼前。
父亲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。那时候,山村尚未通电,周边也没面粉加工厂,人们的生活离不开石碾。一到农闲时节,人们用石碾磨米磨面都要排长队,石碾从早到晚“吱呀吱呀”转个不停,一家接一家,人歇碾不歇。
父亲六岁就被爷爷送到了山外读书,压碾的活自然落到了奶奶和大姑头上。奶奶和大姑每天傍晚从地里回来,还来不及喘口气,就端上一瓢子玉米,或挎着一箢子地瓜干,匆匆忙忙去等碾。一大家子人,就靠这些粮食过活。石碾不停地被人推拉着,周而复始地转着,这家压完了,那家接着倒上。粮食粒子在碾砣和碾盘的磨压下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响声。压碾,一般是年轻人在前面推碾棍,年纪大的在后面扫粮食。父亲放了学偶尔也会去帮忙,他卖力地推着碾棍,奶奶跟在后面,一手扶着碾框,一手用炊帚将压的粮食扫到碾砣中间。不过,父亲推碾的时候并不多,他多数是在石碾旁和小伙伴追打着玩。
压好碾,奶奶会变戏法般把压好的粮食变成各种吃头,要么用玉米面做成金黄的玉米饼子,要么用黄豆面掺上野菜做成香喷喷的“渣豆腐”。最重要的是给在外上学的父亲留出足够的粮食,摊成煎饼。
后来,压碾这活落在了刚过门的大娘身上。父亲那时在县城读高中,一个月回家一趟,只要有空,他就会帮着大娘推碾。随着生活一天天好起来,石碾边上也越来越热闹,特别是进入腊月,乡邻们开始置办年前年后的饭食,天蒙蒙亮,“吱吱呀呀”的压碾声便不绝于耳。乡亲们把碾棍、瓢子、簸箕一字儿摆开等碾,等碾的人越聚越多,不时传来阵阵说笑声。孩子追逐打闹,老人搬张板凳,到石碾边解闷歇乏。大闺女、小媳妇纳着鞋底唠着嗑。婶子、大娘你帮我推几圈,我帮你压一会儿,其乐融融。
再后来,父亲考上大学,远离了山村,把奶奶也接了出来。每年秋天,乡亲们都会压一些诸如小米茶汤面、花椒面、地瓜面、豆扁子这些小吃食给我们送来,说石碾压出来的味道香。
大石碾子圈圈转,黄豆小米磨成面。虽然石碾被岁月暂时搁浅,置身他乡的我却时常忆起。不管过去多少年,也不管走多远,圆圆的碾砣,圆圆的碾盘,都会在我的脑海里“吱吱呀呀”地转动,回响在我的内心深处。